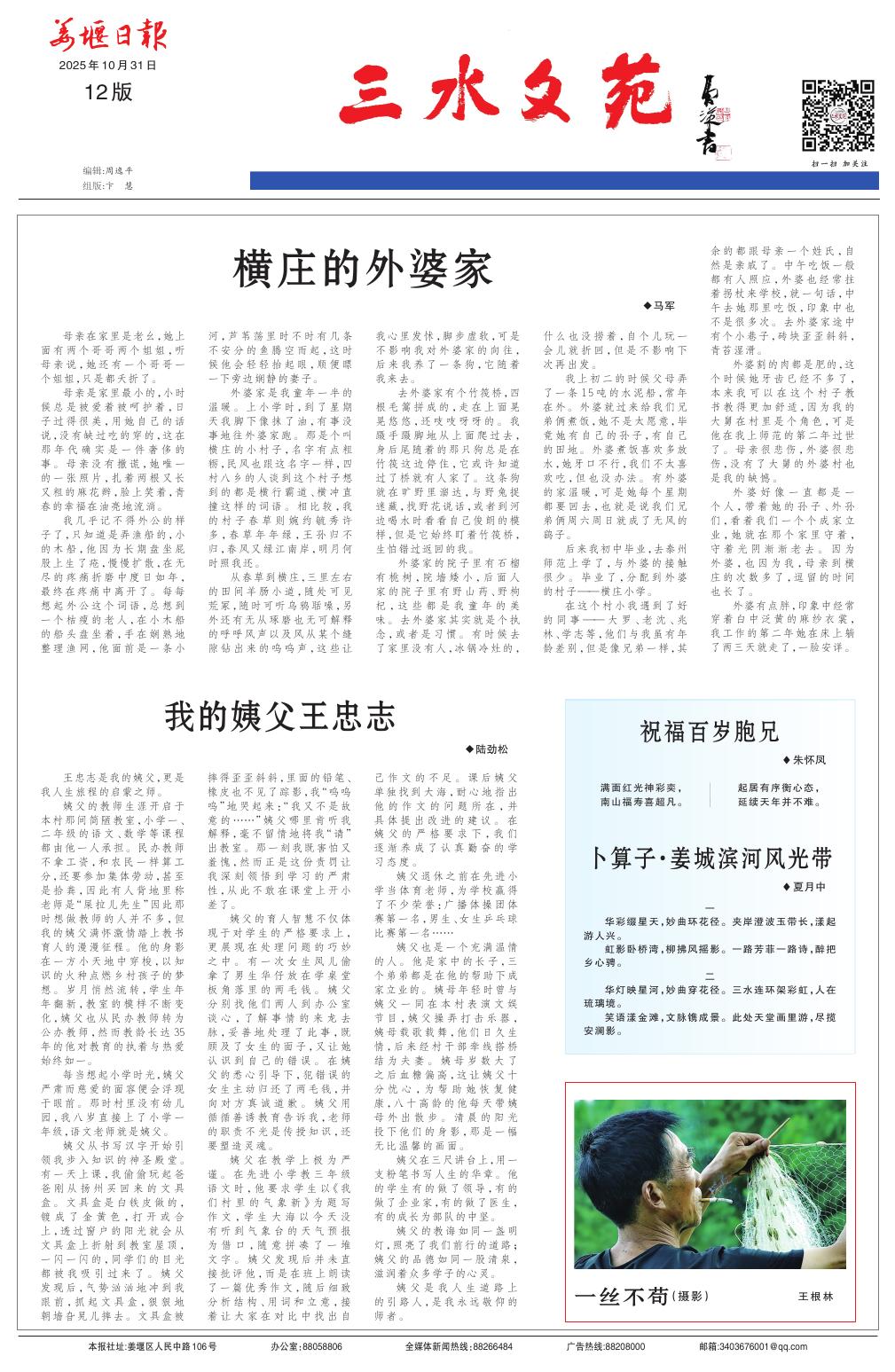еҶ…е®№иҜҰжғ…
2025е№ҙ10жңҲ31ж—Ҙ
жЁӘеә„зҡ„еӨ–е©Ҷ家
жң¬ж–Үеӯ—ж•°пјҡ1387
в—Ҷ马еҶӣ
жҜҚдәІеңЁе®¶йҮҢжҳҜиҖҒе№әпјҢеҘ№дёҠйқўжңүдёӨдёӘе“Ҙе“ҘдёӨдёӘе§җе§җпјҢеҗ¬жҜҚдәІиҜҙпјҢеҘ№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е“Ҙе“ҘдёҖдёӘе§җе§җпјҢеҸӘжҳҜйғҪеӨӯжҠҳдәҶгҖӮ
жҜҚдәІжҳҜ家йҮҢжңҖе°Ҹзҡ„пјҢе°Ҹж—¶еҖҷжҖ»жҳҜиў«зҲұзқҖиў«е‘өжҠӨзқҖпјҢж—ҘеӯҗиҝҮеҫ—еҫҲзҫҺпјҢз”ЁеҘ№иҮӘе·ұзҡ„иҜқиҜҙпјҢжІЎжңүзјәиҝҮеҗғзҡ„з©ҝзҡ„пјҢиҝҷеңЁйӮЈе№ҙд»ЈзЎ®е®һжҳҜдёҖ件еҘўдҫҲзҡ„дәӢгҖӮжҜҚдәІжІЎжңүж’’и°ҺпјҢеҘ№е”ҜдёҖзҡ„дёҖеј з…§зүҮпјҢжүҺзқҖдёӨж №еҸҲй•ҝеҸҲзІ—зҡ„йә»иҠұиҫ«пјҢи„ёдёҠ笑зқҖпјҢйқ’жҳҘзҡ„е№ёзҰҸеңЁжІ№дә®ең°жөҒж·ҢгҖӮ
жҲ‘еҮ д№Һи®°дёҚеҫ—еӨ–е…¬зҡ„ж ·еӯҗдәҶпјҢеҸӘзҹҘйҒ“жҳҜеј„жё”иҲ№зҡ„пјҢе°Ҹзҡ„жңЁиҲ№пјҢд»–еӣ дёәй•ҝжңҹзӣҳеқҗеұҒиӮЎдёҠз”ҹдәҶз–®пјҢж…ўж…ўжү©ж•ЈпјҢеңЁж— е°Ҫзҡ„з–јз—ӣжҠҳзЈЁдёӯеәҰж—ҘеҰӮе№ҙпјҢжңҖз»ҲеңЁз–јз—ӣдёӯзҰ»ејҖдәҶгҖӮжҜҸжҜҸжғіиө·еӨ–е…¬иҝҷдёӘиҜҚиҜӯпјҢжҖ»жғіеҲ°дёҖдёӘжһҜзҳҰзҡ„иҖҒдәәпјҢеңЁе°ҸжңЁиҲ№зҡ„иҲ№еӨҙзӣҳеқҗзқҖпјҢжүӢеңЁеЁҙзҶҹең°ж•ҙзҗҶжё”зҪ‘пјҢд»–йқўеүҚжҳҜдёҖжқЎе°ҸжІіпјҢиҠҰиӢҮиҚЎйҮҢж—¶дёҚж—¶жңүеҮ жқЎдёҚе®үеҲҶзҡ„йұји…ҫз©әиҖҢиө·пјҢиҝҷж—¶еҖҷд»–дјҡиҪ»иҪ»жҠ¬иө·зңјпјҢйЎәдҫҝзһҹдёҖдёӢж—Ғиҫ№еЁҙйқҷзҡ„еҰ»еӯҗгҖӮ
еӨ–е©Ҷ家жҳҜжҲ‘з«Ҙе№ҙдёҖеҚҠзҡ„жё©жҡ–гҖӮдёҠе°ҸеӯҰж—¶пјҢеҲ°дәҶжҳҹжңҹеӨ©жҲ‘и„ҡдёӢеғҸжҠ№дәҶжІ№пјҢжңүдәӢжІЎдәӢең°еҫҖеӨ–е©Ҷ家跑гҖӮйӮЈжҳҜдёӘеҸ«жЁӘеә„зҡ„е°Ҹжқ‘еӯҗпјҢеҗҚеӯ—жңүзӮ№зІ—зІқпјҢж°‘йЈҺд№ҹи·ҹиҝҷеҗҚеӯ—дёҖж ·пјҢеӣӣжқ‘е…«д№Ўзҡ„дәәи°ҲеҲ°иҝҷдёӘжқ‘еӯҗжғіеҲ°зҡ„йғҪжҳҜжЁӘиЎҢйңёйҒ“гҖҒжЁӘеҶІзӣҙж’һиҝҷж ·зҡ„иҜҚиҜӯгҖӮзӣёжҜ”иҫғпјҢжҲ‘зҡ„жқ‘еӯҗжҳҘиҚүеҲҷе©үзәҰжҜ“з§Җи®ёеӨҡпјҢжҳҘиҚүе№ҙе№ҙз»ҝпјҢзҺӢеӯҷеҪ’дёҚеҪ’пјҢжҳҘйЈҺеҸҲз»ҝжұҹеҚ—еІёпјҢжҳҺжңҲдҪ•ж—¶з…§жҲ‘иҝҳгҖӮ
д»ҺжҳҘиҚүеҲ°жЁӘеә„пјҢдёүйҮҢе·ҰеҸізҡ„з”°й—ҙзҫҠиӮ е°ҸйҒ“пјҢйҡҸеӨ„еҸҜи§ҒиҚ’еҶўпјҢйҡҸж—¶еҸҜеҗ¬д№ҢйёҰиҒ’еҷӘпјҢеҸҰеӨ–иҝҳжңүж— д»ҺзҗўзЈЁд№ҹж— еҸҜи§ЈйҮҠзҡ„е‘је‘јйЈҺеЈ°д»ҘеҸҠйЈҺд»ҺжҹҗдёӘзјқйҡҷй’»еҮәжқҘзҡ„е‘ңе‘ңеЈ°пјҢиҝҷдәӣи®©жҲ‘еҝғйҮҢеҸ‘жҖөпјҢи„ҡжӯҘиҷҡиҪҜпјҢеҸҜжҳҜдёҚеҪұе“ҚжҲ‘еҜ№еӨ–е©Ҷ家зҡ„еҗ‘еҫҖпјҢеҗҺжқҘжҲ‘е…»дәҶдёҖжқЎзӢ—пјҢе®ғйҡҸзқҖжҲ‘жқҘеҺ»гҖӮ
еҺ»еӨ–е©Ҷ家жңүдёӘз«№зӯҸжЎҘпјҢеӣӣж №жҜӣзҜҷжӢјжҲҗзҡ„пјҢиө°еңЁдёҠйқўжҷғжҷғжӮ жӮ пјҢиҝҳеҗұеҗұе‘Җе‘Җзҡ„гҖӮжҲ‘蹑жүӢ蹑и„ҡең°д»ҺдёҠйқўзҲ¬иҝҮеҺ»пјҢиә«еҗҺе°ҫйҡҸзқҖзҡ„йӮЈеҸӘзӢ—жҖ»жҳҜеңЁз«№зӯҸиҝҷиҫ№еҒңдҪҸпјҢе®ғжҲ–и®ёзҹҘйҒ“иҝҮдәҶжЎҘе°ұжңүдәә家дәҶгҖӮиҝҷжқЎзӢ—е°ұеңЁж—·йҮҺйҮҢжәңиҫҫпјҢдёҺйҮҺе…”жҚүиҝ·и—ҸпјҢжүҫйҮҺиҠұиҜҙиҜқпјҢжҲ–иҖ…еҲ°жІіиҫ№е–қж°ҙж—¶зңӢзңӢиҮӘе·ұдҝҠжң—зҡ„жЁЎж ·пјҢдҪҶжҳҜе®ғе§Ӣз»ҲзӣҜзқҖз«№зӯҸжЎҘпјҢз”ҹжҖ•й”ҷиҝҮиҝ”еӣһзҡ„жҲ‘гҖӮ
еӨ–е©Ҷ家зҡ„йҷўеӯҗйҮҢжңүзҹіжҰҙжңүжЎғж ‘пјҢйҷўеўҷзҹ®е°ҸпјҢеҗҺйқўдәә家зҡ„йҷўеӯҗйҮҢжңүйҮҺеұұиҚҜгҖҒйҮҺжһёжқһпјҢиҝҷдәӣйғҪжҳҜжҲ‘з«Ҙе№ҙзҡ„зҫҺе‘ігҖӮеҺ»еӨ–е©Ҷ家其е®һе°ұжҳҜдёӘжү§еҝөпјҢжҲ–иҖ…жҳҜд№ жғҜгҖӮжңүж—¶еҖҷеҺ»дәҶ家йҮҢжІЎжңүдәәпјҢеҶ°й”…еҶ·зҒ¶зҡ„пјҢд»Җд№Ҳд№ҹжІЎжҚһзқҖпјҢиҮӘдёӘе„ҝзҺ©дёҖдјҡе„ҝе°ұжҠҳеӣһпјҢдҪҶжҳҜдёҚеҪұе“ҚдёӢж¬ЎеҶҚеҮәеҸ‘гҖӮ
жҲ‘дёҠеҲқдәҢзҡ„ж—¶еҖҷзҲ¶жҜҚеј„дәҶдёҖжқЎ15еҗЁзҡ„ж°ҙжіҘиҲ№пјҢеёёе№ҙеңЁеӨ–гҖӮеӨ–е©Ҷе°ұиҝҮжқҘз»ҷжҲ‘们兄ејҹдҝ©з…®йҘӯпјҢеҘ№дёҚжҳҜеӨӘж„ҝж„ҸпјҢжҜ•з«ҹеҘ№жңүиҮӘе·ұзҡ„еӯҷеӯҗпјҢжңүиҮӘе·ұзҡ„з”°ең°гҖӮеӨ–е©Ҷз…®йҘӯе–ңж¬ўеӨҡж”ҫж°ҙпјҢеҘ№зүҷеҸЈдёҚиЎҢпјҢжҲ‘们дёҚеӨӘе–ңж¬ўеҗғпјҢдҪҶд№ҹжІЎеҠһжі•гҖӮжңүеӨ–е©Ҷзҡ„家温жҡ–пјҢеҸҜжҳҜеҘ№жҜҸдёӘжҳҹжңҹйғҪиҰҒеӣһеҺ»пјҢд№ҹе°ұжҳҜиҜҙжҲ‘们兄ејҹдҝ©е‘Ёе…ӯе‘Ёж—Ҙе°ұжҲҗдәҶж— йЈҺзҡ„й№һеӯҗгҖӮ
еҗҺжқҘжҲ‘еҲқдёӯжҜ•дёҡпјҢеҺ»жі°е·һеёҲиҢғдёҠеӯҰдәҶпјҢдёҺеӨ–е©Ҷзҡ„жҺҘи§ҰеҫҲе°‘гҖӮжҜ•дёҡдәҶпјҢеҲҶй…ҚеҲ°еӨ–е©Ҷзҡ„жқ‘еӯҗ——жЁӘеә„е°ҸеӯҰгҖӮ
еңЁиҝҷдёӘжқ‘е°ҸжҲ‘йҒҮеҲ°дәҶеҘҪзҡ„еҗҢдәӢ——еӨ§зҪ—гҖҒиҖҒжІҲгҖҒе…Ҷжһ—гҖҒеӯҰеҝ—зӯүпјҢ他们дёҺжҲ‘иҷҪжңүе№ҙйҫ„е·®еҲ«пјҢдҪҶжҳҜеғҸе…„ејҹдёҖж ·пјҢе…¶дҪҷзҡ„йғҪи·ҹжҜҚдәІдёҖдёӘ姓ж°ҸпјҢиҮӘ然жҳҜдәІжҲҡдәҶгҖӮдёӯеҚҲеҗғйҘӯдёҖиҲ¬йғҪжңүдәәз…§еә”пјҢеӨ–е©Ҷд№ҹз»ҸеёёжӢ„зқҖжӢҗжқ–жқҘеӯҰж ЎпјҢе°ұдёҖеҸҘиҜқпјҢдёӯеҚҲеҺ»еҘ№йӮЈйҮҢеҗғйҘӯпјҢеҚ°иұЎдёӯд№ҹдёҚжҳҜеҫҲеӨҡж¬ЎгҖӮеҺ»еӨ–е©Ҷ家йҖ”дёӯжңүдёӘе°Ҹе··еӯҗпјҢз –еқ—жӯӘжӯӘж–ңж–ңпјҢйқ’иӢ”ж№ҝж»‘гҖӮ
еӨ–е©ҶеүІзҡ„иӮүйғҪжҳҜиӮҘзҡ„пјҢиҝҷдёӘж—¶еҖҷеҘ№зүҷйҪҝе·Із»ҸдёҚеӨҡдәҶпјҢжң¬жқҘжҲ‘еҸҜд»ҘеңЁиҝҷдёӘжқ‘еӯҗж•ҷд№Ұж•ҷеҫ—жӣҙеҠ иҲ’йҖӮпјҢеӣ дёәжҲ‘зҡ„еӨ§иҲ…еңЁжқ‘йҮҢжҳҜдёӘи§’иүІпјҢеҸҜжҳҜд»–еңЁжҲ‘дёҠеёҲиҢғзҡ„第дәҢе№ҙиҝҮдё–дәҶгҖӮжҜҚдәІеҫҲжӮІдјӨпјҢеӨ–е©ҶеҫҲжӮІдјӨпјҢжІЎжңүдәҶеӨ§иҲ…зҡ„еӨ–е©Ҷжқ‘д№ҹжҳҜжҲ‘зҡ„зјәжҶҫгҖӮ
еӨ–е©ҶеҘҪеғҸдёҖзӣҙйғҪжҳҜ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еёҰзқҖеҘ№зҡ„еӯҷеӯҗгҖҒеӨ–еӯҷ们пјҢзңӢзқҖжҲ‘们дёҖдёӘдёӘжҲҗ家з«ӢдёҡпјҢеҘ№е°ұеңЁйӮЈдёӘ家йҮҢе®ҲзқҖпјҢе®ҲзқҖе…үйҳҙжёҗжёҗиҖҒеҺ»гҖӮеӣ дёәеӨ–е©ҶпјҢд№ҹеӣ дёәжҲ‘пјҢжҜҚдәІеҲ°жЁӘеә„зҡ„ж¬Ўж•°еӨҡдәҶпјҢйҖ—з•ҷзҡ„ж—¶й—ҙд№ҹй•ҝдәҶгҖӮ
еӨ–е©ҶжңүзӮ№иғ–пјҢеҚ°иұЎдёӯз»Ҹеёёз©ҝзқҖзҷҪдёӯжіӣй»„зҡ„йә»зәұиЎЈиЈіпјҢжҲ‘е·ҘдҪңзҡ„第дәҢе№ҙеҘ№еңЁеәҠдёҠиәәдәҶдёӨдёүеӨ©е°ұиө°дәҶпјҢдёҖи„ёе®үиҜҰ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