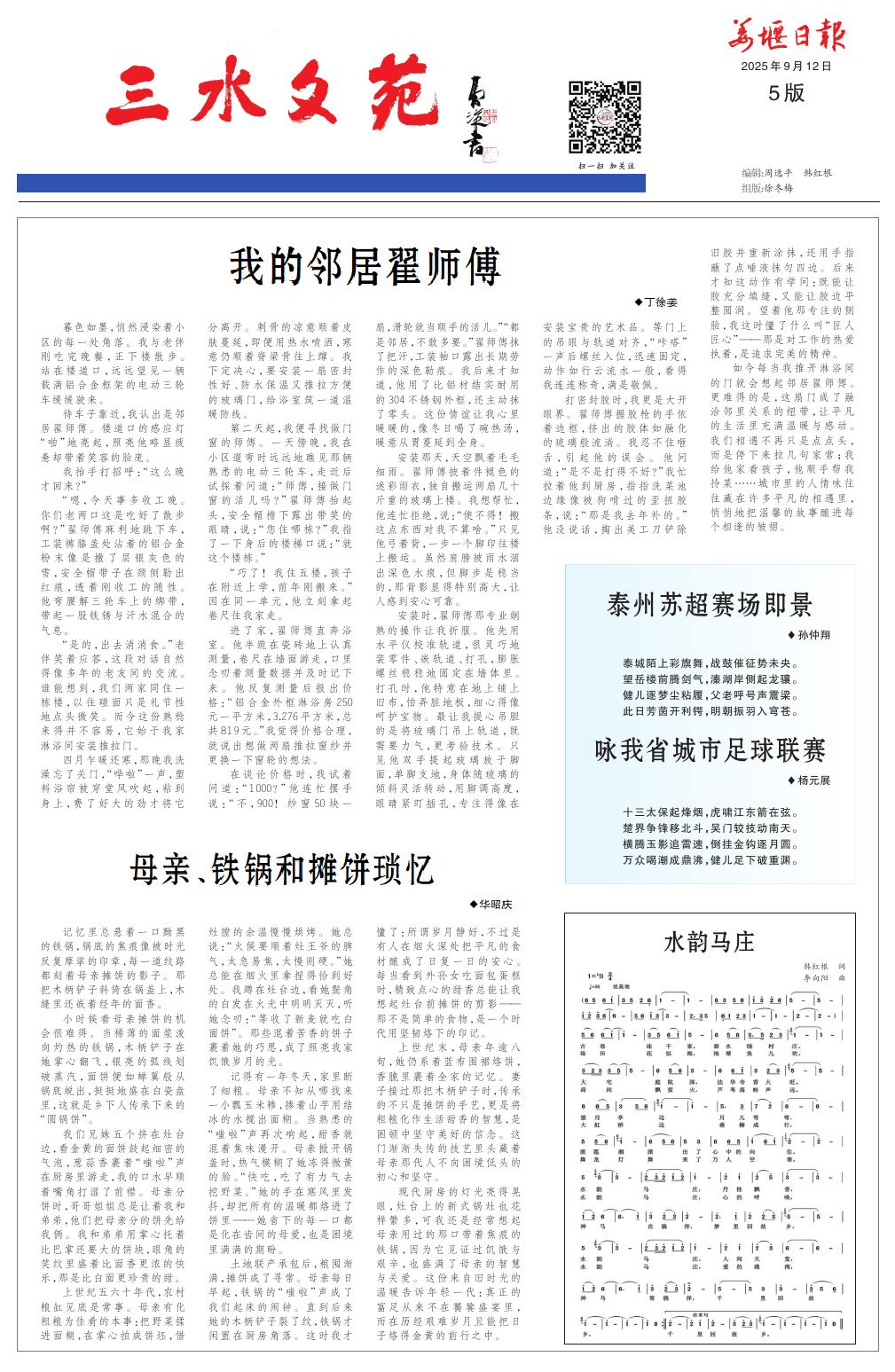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9月12日
母亲、铁锅和摊饼琐忆
本文字数:1049
◆华昭庆
记忆里总悬着一口黝黑的铁锅,锅底的焦痕像被时光反复摩挲的印章,每一道纹路都刻着母亲摊饼的影子。那把木柄铲子斜倚在锅盖上,木缝里还嵌着经年的面香。
小时候看母亲摊饼的机会很难得。当稀薄的面浆泼向灼热的铁锅,木柄铲子在她掌心翻飞,银亮的弧线划破蒸汽,面饼便如蝉翼般从锅底蜕出,挺挺地盛在白瓷盘里,这就是乡下人传承下来的“圆锅饼”。
我们兄妹五个挤在灶台边,看金黄的面饼鼓起细密的气泡,葱蒜香裹着“嗤啦”声在厨房里游走,我的口水早顺着嘴角打湿了前襟。母亲分饼时,哥哥姐姐总是让着我和弟弟,他们把母亲分的饼先给我俩。我和弟弟用掌心托着比巴掌还要大的饼块,眼角的笑纹里盛着比面香更浓的快乐,那是比白面更珍贵的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粮缸见底是常事。母亲有化粗粮为佳肴的本事:把野菜揉进面糊,在掌心拍成饼坯,借灶膛的余温慢慢烘烤。她总说:“火候要顺着灶王爷的脾气,太急易焦,太慢则硬。”她总能在烟火里拿捏得恰到好处。我蹲在灶台边,看她鬓角的白发在火光中明明灭灭,听她念叨:“等收了新麦就吃白面饼”。那些混着苦香的饼子裹着她的巧思,成了照亮我家饥饿岁月的光。
记得有一年冬天,家里断了细粮。母亲不知从哪找来一小瓢玉米糁,掺着山芋用结冰的水搅出面糊。当熟悉的“嗤啦”声再次响起,甜香就混着焦味漫开。母亲掀开锅盖时,热气模糊了她冻得微黄的脸。“快吃,吃了有力气去挖野菜。”她的手在寒风里发抖,却把所有的温暖都烙进了饼里——她省下的每一口都是化在齿间的母爱,也是困境里满满的期盼。
土地联产承包后,粮囤渐满,摊饼成了寻常。母亲每日早起,铁锅的“嗤啦”声成了我们起床的闹钟。直到后来她的木柄铲子裂了纹,铁锅才闲置在厨房角落。这时我才懂了: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烟火深处把平凡的食材酿成了日复一日的安心。每当看到外孙女吃面包蛋糕时,精致点心的甜香总能让我想起灶台前摊饼的剪影——那不是简单的食物,是一个时代用坚韧烙下的印记。
上世纪末,母亲年逾八旬,她仍系着蓝布围裙烙饼,香脆里裹着全家的记忆。妻子接过那把木柄铲子时,传承的不只是摊饼的手艺,更是将粗粮化作生活甜香的智慧,是困顿中坚守美好的信念。这门渐渐失传的技艺里头藏着母亲那代人不向困境低头的初心和坚守。
现代厨房的灯光亮得晃眼,灶台上的新式锅灶也花样繁多,可我还是经常想起母亲用过的那口带着焦痕的铁锅,因为它见证过饥饿与艰辛,也盛满了母亲的智慧与关爱。这份来自旧时光的温暖告诉年轻一代: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饕餮盛宴里,而在历经艰难岁月且能把日子烙得金黄的前行之中。